

「房子賣了?」 我站在客廳,看著周遠。 他坐在沙發上,翹著二郎腿,連眼皮都沒抬一下。 「賣了。580萬,全款。」 我的手在發抖。 那是我們的婚房。首付120萬,是我爸媽賣了老家的房子湊的。房貸每月1萬5,我還了整整4年。 「我沒簽字。」 「不需要。」周遠終于看了我一眼,「房子是我的名字,我想賣就賣,你管得著嗎?」 我盯著他。 結婚5年,我第一次覺得這個男人如此陌生。 「那合同上的簽名,」我的聲音很輕,「是誰幫我籤的?」 周遠的表情僵了一瞬。 我笑了。


丈夫和那個女人,深夜不歸 同學聚會結束後,丈夫坐上了白月光許念夏的車。 有人打趣:「小時候就是一對兒,現在十年沒見了,你們倆復合唄。」 「這要看吳樾的意思。」 許念夏淡淡笑著,卻掩飾不住喜悅。 我丈夫露出笑容,沒有回答,卻也沒有拒絕。 眾人開始起鬨。 我忍不住給他們鼓掌。


電視里,前夫談到有一次在飛機上寫遺書。 寫完卻遲遲沒有發送。主持人戲謔:「是不是無膽啊?」 他愣了愣,拙劣模仿一口粵語,望著人群挑釁道:「係呀,我無膽啦,她嫁的香港佬還要養我的細路仔啦!」 觀眾哄堂大笑。 唯有我老公坐在下面,面無表情。


出月子後,婆婆忽然中風了。 老公盯著我還剩三個月的產休假,說: 「現在只能你來照顧媽了。」 我沒反對,只是問他: 「怎麼照顧?」 老公有些不耐煩: 「媽怎麼照顧你月子,你就怎麼照顧媽,這還要我教嗎?」 這樣啊,那我就明白了,老公也沒那麼孝順嘛。 月子仇可以當場報了。


十八歲那年,我無意間撞破周陵川和一個女生接吻。 二十歲,他和女友情難自抑,搬到校外開始同居。 二十二歲,他在朋友圈曬出婚戒,官宣訂婚。 二十五歲,朋友忽然告訴我,周陵川和初戀分手。 他很受打擊,幾乎一蹶不振。 同年,他酒醉將我認錯,我們糾纏了一夜。 第二日清晨,他望著床單上刺目血紅。 沉默很久,啞聲說他會負責。 二十八歲,我有了身孕。 滿懷歡喜準備告訴他好消息時。 他卻先一步開了口:「詠慈,她回來了。」 「很抱歉,這幾年我從未忘記過她。」 「只要你不鬧,安守本分,周太太仍然會是你。」 他捏捏眉心,冷漠看著我: 「畢竟,你當年接近我,圖的不就是這些?」


媽媽臨終前告訴我,我有三個親生哥哥。 于是我背著蛇皮袋進城找哥哥。 可進城才發現,原來我的哥哥們竟是金融新貴、頂流明星、電競天才……




相愛11年的丈夫同我說: “我們離婚吧,我想給她一個名分。” 第二天,我們就去了民政局。 從那天起他就沒有回過家,只是從朋友圈不斷傳來他們的訊息。 而我也放棄對他公司的一切幫助,只看他自己能走多遠。


我提離婚時,老伴正在做飯。 她的手微微一顫,輕聲回答:「好。」 這已經是我第10次提離婚了。 前9次,她像個瘋子一樣又哭又鬧,說讓半截身子入土的人離婚,簡直是逼她去死。 我煩透了她身上的老人味,不像我的情人,充滿生命力。 沒想到,這次她竟然答應了。 答應得太過輕巧,彷彿只是在回答今天吃什麼。 我看著她在廚房忙碌的背影。 欣喜之餘,卻莫名地不安起來......


陸川霽不愛我了,我知道,自從那件事後,他開始嫌棄我了。 他是我的青梅竹馬,曾信誓旦旦對我說,會一輩子和我在一起。 後來,他遇見另一個幹凈明媚的女孩子。 「薇薇,我一直拿你當妹妹看的。」


我的叔叔大我 12 歲,他教了我很多第一次。 我喜歡他,卻不喜歡他帶回來的女人。 我躲在他臥室門外聽著裡面的聲音,心如刀絞。


結婚兩年,徐靖州的白月光離婚回國。 當晚,從不夜不歸宿的他,第一次沒有回家。 當初徐靖州他媽曾開價五百萬逼我離開,我沒答應。 現在我想通了,準備還還價,還到一千萬就離婚。 畢竟,她相中的兒媳婦現在離婚了,自由了,我騰位置,她老人家一定很高興。 早晨六點,我敲響了婆婆的房門。 十分鐘後,整個徐家炸了鍋。 兩個小時後,徐靖州收到了我簽好字的離婚協議。 當晚,我在酒吧和小奶狗弟弟貼面熱舞的時候,徐靖州的人……把酒吧封了? #婚姻 #破鏡重圓 #現代


結婚五年,我終于懷孕,正要告訴司南潯這個好消息時,卻聽見婆婆問他: 「安晴那邊你打算什麼時候跟她開口?小溪已經顯懷了,我們司家不能無後。」 「再等等,給我一點時間,我會處理好。」 我靠在門口,默默收回孕檢單。 司南潯,你的承諾,一文不值。 ……


江宴的好兄弟新開了家高檔會所。 他哄我說,算是給對方捧場,他只會去一次。 可後來卻去了一次又一次。 「林瑤可憐,爹不疼娘不愛的,年紀輕輕就被迫來這裡討生活。」 所以才要常去給她撐腰。 我無法理解,便打算親自去會所一趟。 卻意外撞見正被欺負的宋舟。 同樣的爹不疼娘不愛,他還多個病弱的小妹。 看著少年清冷破碎的模樣。 我想,或許我也可以給他撐個腰。


穿書女離開了我的身體時,已經六年過去了。 我睜開眼,以為一切都可以回到從前,卻見陳柯冷笑: 「裝失憶,這又是你的新招數?」 我愣愣看清了他的臉,然後猛地上前掐住他脖子,歇斯底里: 「顧明夜呢?!顧明夜在哪裡?!我怎麼會嫁給你?!」 明明六年前,我懷孕了,我們說好要結婚的啊!


我正在超市排隊搶打折雞蛋,突然看到了彈幕。 【這就是男主念念不忘的白月光吧?】 【仔細看看,女配長得確實很像她……】 【就因為這個,男主一直無條件偏心女配,女主怎麼爭都沒用。】 【女主抑鬱了好多年,直到查出癌症,男主才幡然醒悟。】 我一個激靈,震驚地愣在原地。 白月光?? 可是,我已經五十歲了啊。


穿成無腦文裡的惡毒女主,我擺爛了。 系統讓我羞辱後媽,我照做。 讓我陷害女配,我照做。 讓我搶男主? 我反手把男主推給女配:搞男人哪有搞錢爽,別耽誤我搞錢。 系統沉默兩秒,最後憋出一句:【你厲害。】 我賺得盆滿缽滿,家人朋友全補齊,人生爽到飛起。 可下一秒,卻猛地驚醒。 新來的總裁寵溺地看著我: 「方經理,你跳《小蘋果》扭胯那一下,還能再標準點。」 我:!!


過年關,行業旺季,我接了個大單。 【一天一萬,家長紅包可自留。要求:乖巧。】 于是大年三十,我穿著粉色套裝扎著馬尾,敲響了僱主家的大門。 可開門的,竟然是我的前男友。 他愣了兩秒,然後笑了:「穿這麼乖,來求復合?」 還沒來得及開口,我的僱主從他身後啪嗒啪嗒跑來,一把將他扒拉開。 「讓讓讓讓!我女朋友來了!」 他攬過我的肩,挑眉嘚瑟:「怎麼樣,哥女朋友漂亮吧?」


我死後,閻王給我兩個選項。 一是消除全部記憶,重新轉世為人。 二是帶著全部記憶,下輩子做一條狗。 我想了想。 「我選擇狗。」 敲錘定音。 我重新開啟了我的人生。 啊不。 狗生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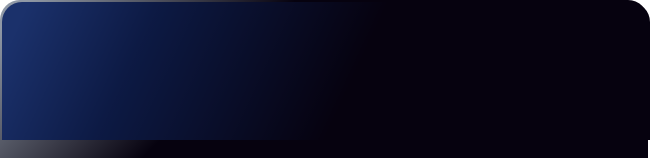



 信用卡(台灣)
信用卡(台灣)
 Paypal/信用卡
Paypal/信用卡
 聯繫客服
聯繫客服
